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中国学界打开了一扇门,让研究者看到了一大片精彩的风景,在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以我而言,限于外语水平,主要仰仗译本了解海外研究中国的方法、成果与现状,这套丛书是我选购阅读最多的。
如今,丛书主编刘东先生又发心创办了《中国研究文摘》,其思路有两条:一是相比翻译海外研究专著,希望更能及时追踪最有创意的海外中国研究的论文;二是基于舆论空间的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研究专著“很难再被整本地译出”。这里,沿着他的后一思路,谈点延伸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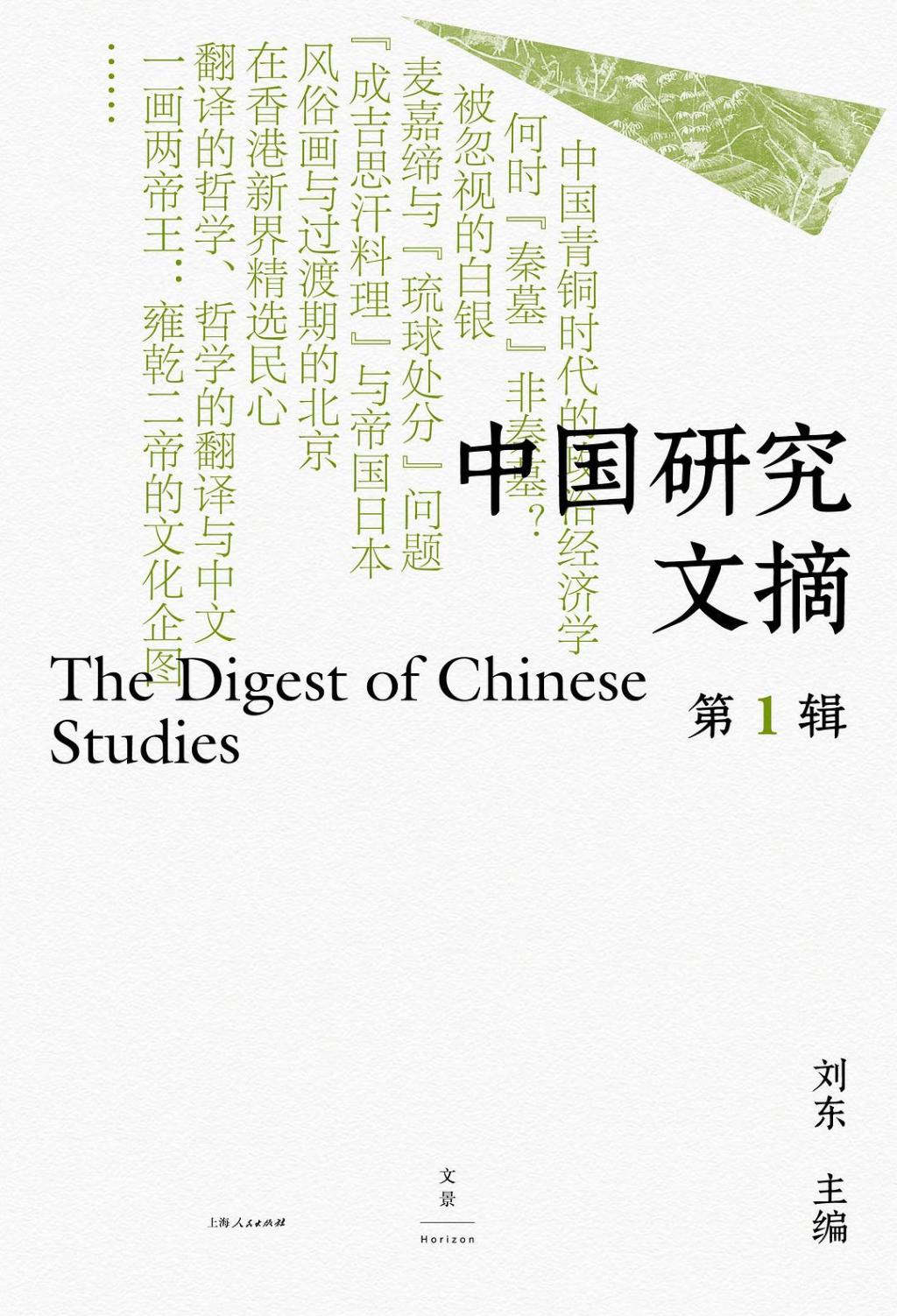
刘东编《中国研究文摘》
舆论空间的松紧尺度,并不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译者与出版方所能自行决定的,但各方能否在大形势下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维护一个“睁眼看世界”的窗口,则是各方应该深长思之的。“睁眼看世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毋庸赘言,否则一个学者,一个学科,乃至一个国家,必然沦为井底之蛙,还洋洋得意地夜郎自大。即便《中国研究文摘》首发词中所说“中国越来越闭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对外部社科资讯的译介也并未完全停止。20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机构翻译出版了所谓的“灰皮书”;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仍创办了《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当时虽标明“供内部参考批判用”,或附上些批判性的按语,但只要窗口没关闭,其价值与功用恐怕就不见得局限在“参考批判”上。
1978年,改革之门大开,舆情随即开放,“睁眼看世界”尤感迫切,当时也来不及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的前沿论著,便创刊了《国外社会科学》,也是设想先打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当然,这时不再标榜批判),而后便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译介西方人文科学著作的高潮。
对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海内外互动,我想在这里略谈几点个人的思考。
首先,对海外中国研究必须坚持自主性与主体性的立场。
中国研究之所以为中国研究,说到底,不是以中国的研究去迎合、证明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方法与成果,而是以海外的研究范式、方法与成果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研究。在这种互动中,中国、中国学界与中国学者始终应该居于自主与主体的地位。
国门乍开初期,一度对外来人文思潮经历过饥不择食与邯郸学步的阶段,随着自身研究的推进,才逐渐实现了自主性与主体性。这在中国宋史学界引进日本与欧美学者的“唐宋变革论”过程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唐宋变革论”最先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他的中国史体系有二大支柱,一是与“宋代近世说”密切关联的“唐宋变革论”,一是“文化中心移动说”以及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
中国学界引入“唐宋变革论”之初,并未警觉内藤解释框架中日本将成为东亚文明中心的主体性意识,随着认识的深化,才明确持排异的态度。其后对日本欧美学者“唐宋变革论”的某些论断,例如以欧洲文艺复兴期的时代特征、城市形态与市民文艺来比附宋代的相关论题,中国学界也很快提出质难与反驳。
在肯定“唐宋变革论”具有契合历史的合理因素时,中国宋史学界也日渐意识到“唐宋变革论”有其有效的边界。有的变化,例如室内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习俗之变就未必能纳入“唐宋变革论”的范畴。学界流行“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的顺口溜,就是嘲讽将这种变革过度泛化。
时至今日,中国学界已经理性地认识到,“唐宋变革论”不是阐释历史的唯一范式,既不能变为取巧偷懒的“方便法门”,更不是包打天下的独门秘技。例如唐宋之际的城镇化趋向,虽然也能援用“唐宋变革论”的研究范式,却不是唯一可以切入的视角,与历史人文地理学相关的视野与方法仍有其用武之地。由于不再局限或照搬“唐宋变革论”,中国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问题,各有其不同的变革与不同的起讫,这种因革的渐进性、过程性与延续性也不是“唐宋变革论”所能全部涵括与诠释的。于是,除了“唐宋变革论”,相继提出了两宋之际转型说、宋元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说等史学命题。
总之,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所有新观点、新理论乃至新范式,秉持多元开放的心态,庶几能真确把脉“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钱穆语)。
其次,对海外中国研究应该奉行拿来主义与为我所用的原则。
既然强调主体性与自主性,中国的中国研究就应该借鉴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方法与成果,构建自己的理论、方法与研究个案。
在这一方面,刘子健作为美籍华人学者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他诘难与挑战“宋代近世说”:“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他批评“宋代近世说”的东西史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欧洲历史当作了度量衡”,二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并进而主张两宋之际中国转向内在说。刘子健此说聚焦于政治文化的转捩,他认为:11世纪到12世纪,宋代“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
我从2016年起重返南宋史研究,首先感到可以借用刘子健的“转向内在”说,同时也受到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启发。他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里概括出一个“绍兴和议体制”或“绍兴十二年体制”。但我认为,“绍兴和议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不论当时,还是后来,其实际内涵已超出了军事与外交的范围,成为南宋赖以立国的政权体制,不妨径称其为“绍兴体制”。我在2019年出版了《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提炼融会了“转向内在”与“绍兴体制”两个命题,对南宋专制政体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证与阐释,也算是拿来主义与为我所用的具体尝试。总之,我们要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化为自己的血肉,然后把它输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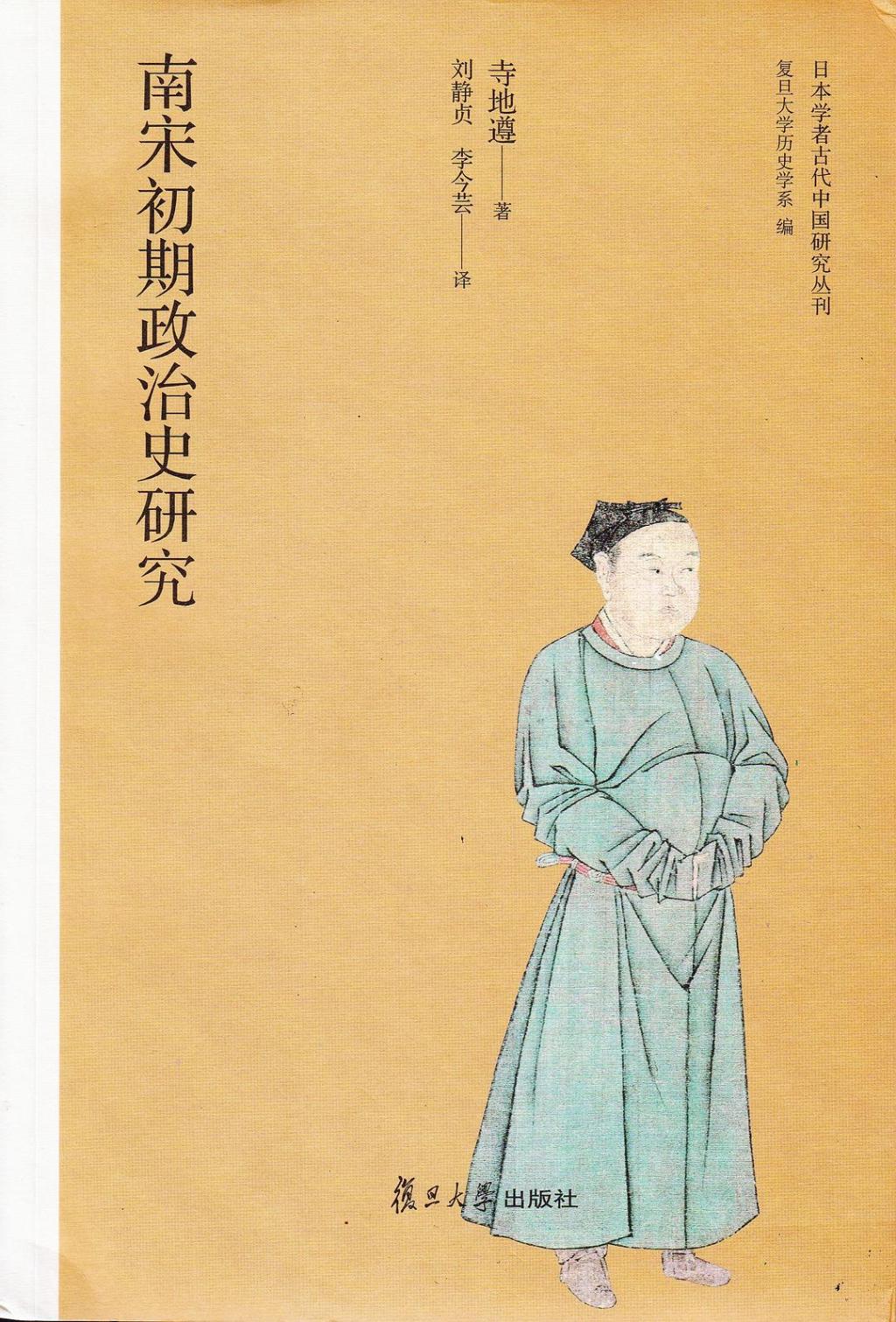
寺地遵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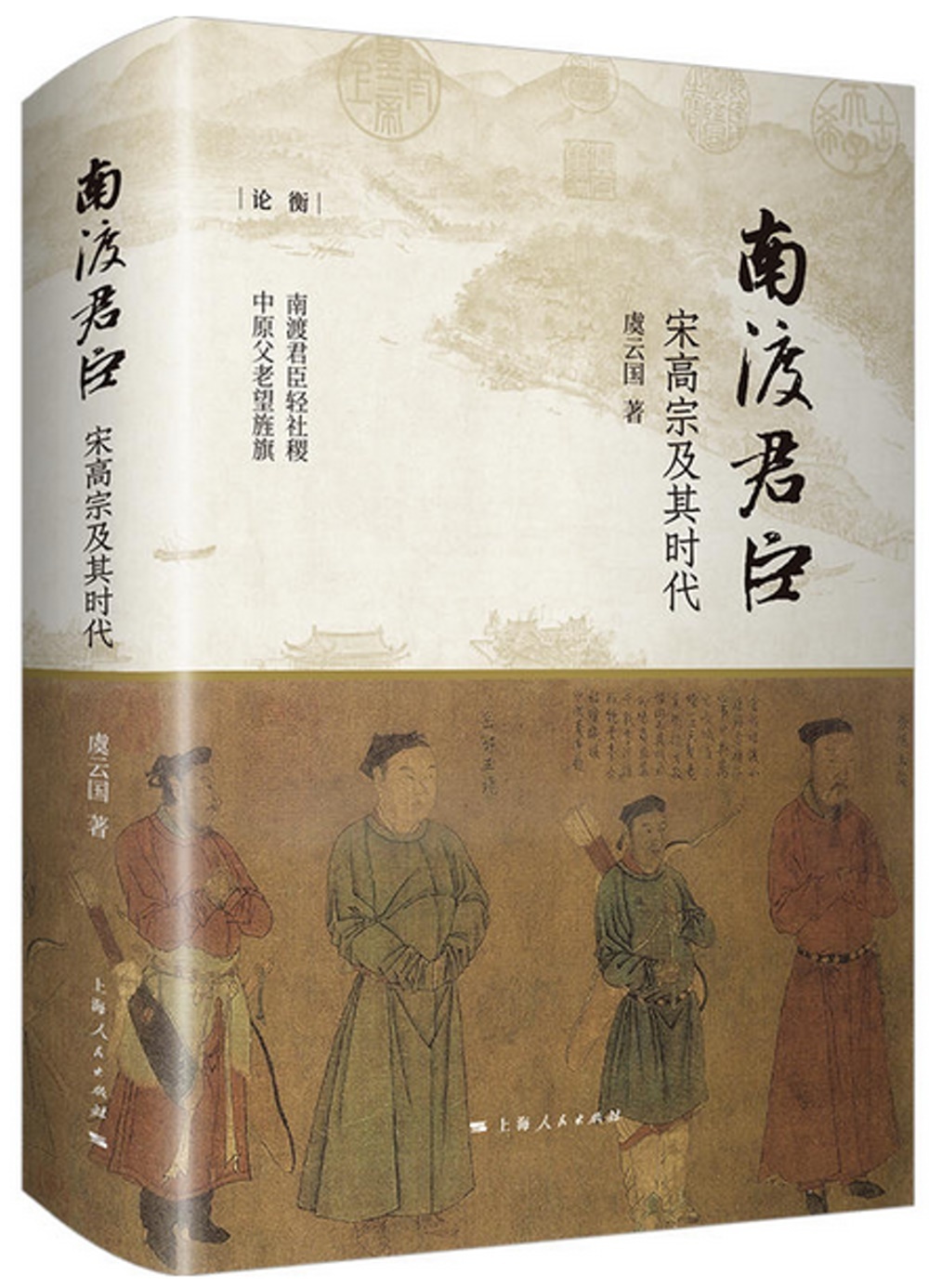
虞云国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
最后,对海外中国研究亟需并重推介与批评的方针。
只要对学科研究真正投入,由于研究的是母国文化,中国学者没有隔靴搔痒之隔膜感,更无隔岸观火之疏离感,最具有历史感与在场感。唯其如此,针对译介引入的海外中国学著作,诚如刘东主编在《中国研究文摘》首发词里所说,不应该“马上不假思索地视其为‘高见’,乃至是可堪师法的、进入流行的‘定见’”,而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学界的优势,及时互动,既要肯定其对学科的新贡献,掘发其中有欠彰显的逻辑线索或潜在话语,也要对其中存在谬误的史观、方法与结论,发出中国学界的声音。应该积极营造商榷批评的学术氛围,只要不是出于恶意的攻击,或上纲上线,在推介的同时鼓励商榷与争鸣,显然有助于海内外中国研究的不断深入。
举例来说,伊沛霞的《宋徽宗:天下一人》堪称近年海外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但著者自称“对徽宗表达出了更多的同情”。中国宋史学者在书评里就特别提醒:“出于同情之心,伊著《徽宗》难免回避一些史实,对史料作选择性处理”;“历史家论历史,力求主客观一致。伊沛霞教授也不例外,她评论宋徽宗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提示对中国读者全面定位这部海外名著绝非可有可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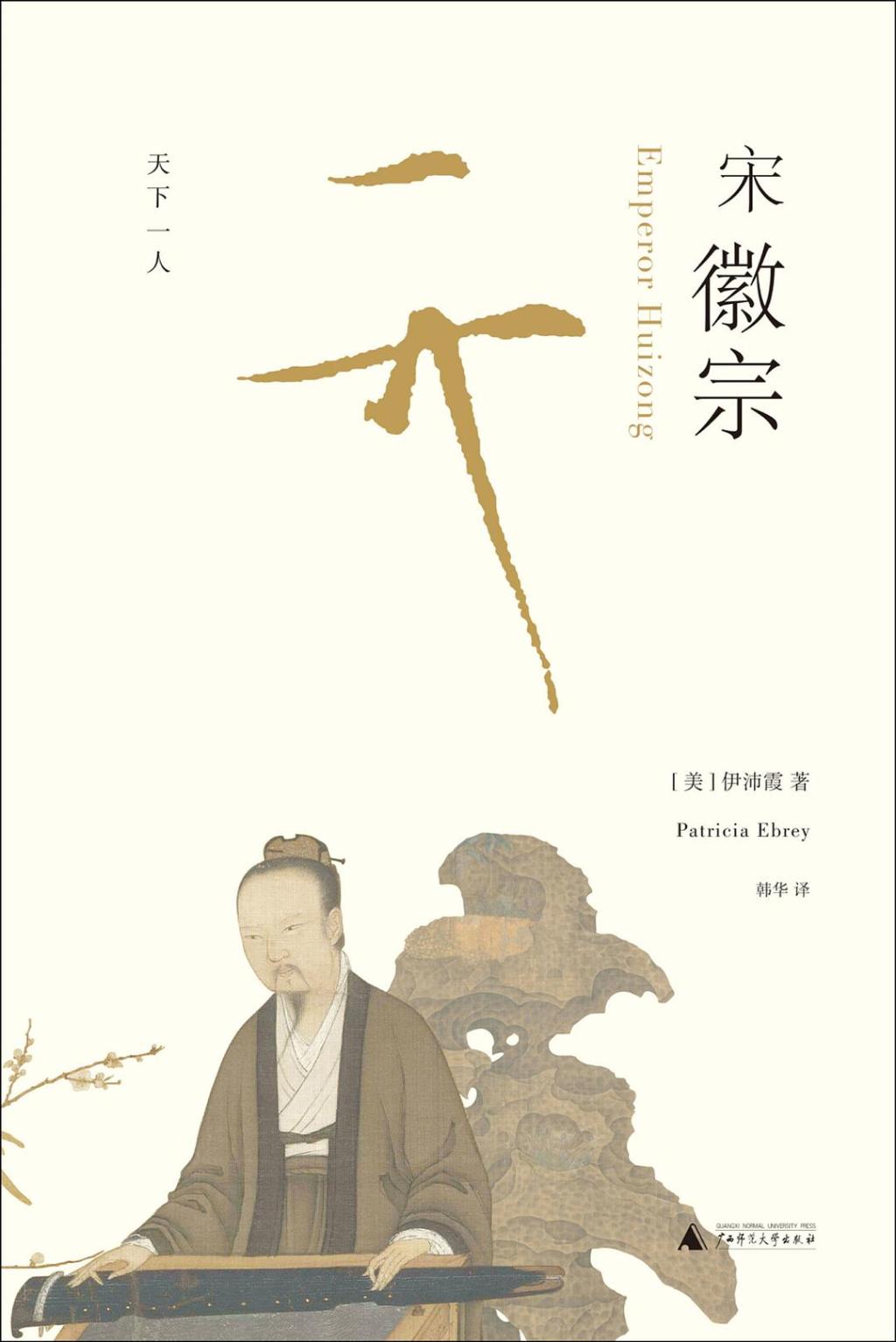
伊沛霞著《宋徽宗:天下一人》
再如,美国学者蔡涵墨著有《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其成功之处有二:一是揭示了秦桧与道学的关系,二是指出道学对南宋史学的影响。但著者以历史解构主义对待有关秦桧的史料,片面断言“涉及的著作年代越早,秦桧的形象反面色彩就越少”,借以辩护秦桧形象与秦桧专政,却无视史料学的基本常识:一是“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二是“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识其人史识何如”。不言而喻,对秦桧专政的负面记忆绝无可能在其专政年代以文字或口述的形式公开流传,只能出现在他倒台之后。但著者过度质疑这种集体记忆拼缀复原的历史实相,不仅在史料方法论上大有瑕疵,而且引导今人对秦桧的评价滑入错误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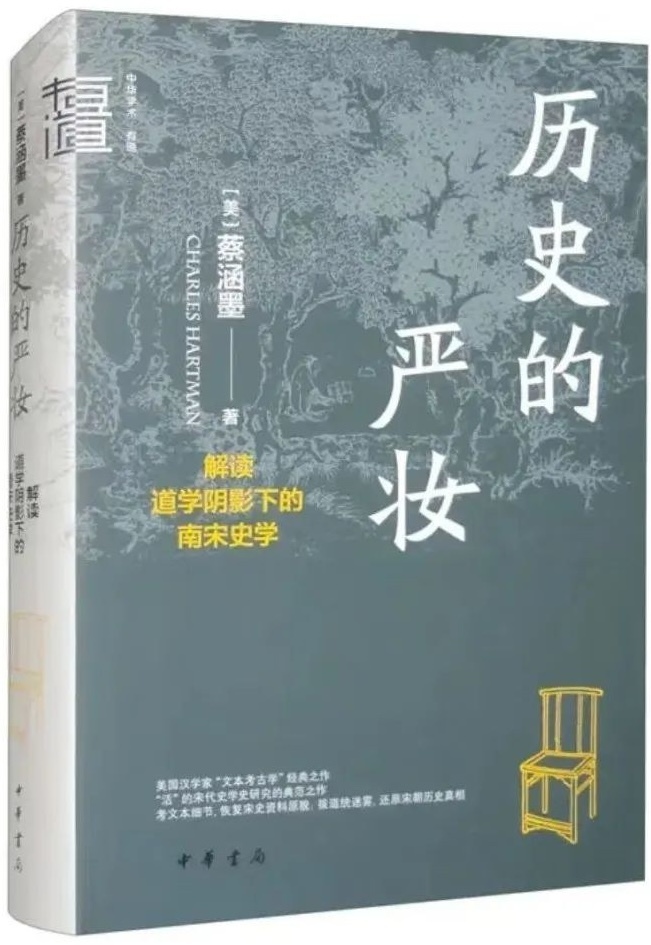
蔡涵墨著《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这种历史解构主义的滥用,一旦在中国史界推衍成风,必然导致中国专制历史上许多专政实相与事件真相遭到无形消解或彻底解构,倘若再与历史上集权专制者对史料的禁毁与篡改相呼应,势必真正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唯其如此,我书评里有感而发:“大洋彼岸的某些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且不苛求有那种感同身受的亲历感,无奈也缺乏那种设身处地的领悟力,在讨论中国史上专政实相时,个别论断总让大洋此岸的中国人感到有点隔膜,也许他们太难在中西古今的不同世界间作出必要的时空切换!”
总之,坚持自主性与主体性的立场,奉行拿来主义与为我所用的原则,倡导推介与批评并重的方针,是我对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海内外互动这一议题的肤浅的思考。由衷期望《中国研究文摘》能更好地为中国学者打开海外中国研究的窗口。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虞云国|对中国研究海内外互动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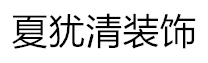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8
京ICP备2025104030号-18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